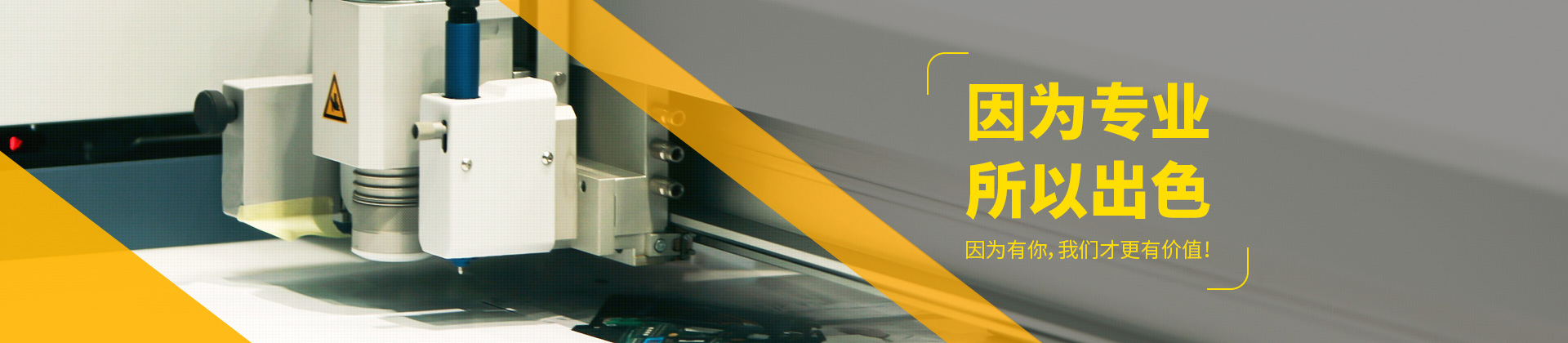逛书店,是旧文人异样的一种读书方法,也是读书人对占有好书的一种“礼仪”。所谓藏书万卷,尤其是占有稀缺的善本、珍本与孤本书本,已成为一种精力财富的夸耀。
儿时,晴天去夫子庙大成殿门口的小人书摊,雨天去朱雀路旁边的一家小人书店,花上两分钱,就能够消磨半响饱看小人书了,假使这种书摊书铺也叫书店的话,那么,我逛书店的嗜好,便是从小养成的爱好。

但是,给我形象最深的,则是贡院西街东西两市一带的白下书肆,那旧书店把卸下的门板搭成的书摊沿街排生长阵,买者和不买者,都是站在那里翻书。多数是来蹭读的揩油者,站在那里盯着一本书读,直到看完,刚才释手,店家也并不驱逐。我想,这也算是商家集合人气的战略吧。还有一种读者,却是在敏捷扫描货摊上一切的书本,偶然拿起一本,翻阅一下版别、目录,便将其放置一边,此后有一搭没一搭向店家探问种种书本的音讯,如有,捎带问一句何种版别。此刻,店家眼里便放出光来,周到有加,搬出椅子看座,端上一杯茶水,这就预示生意的开端,卖者开出高价,买者坐地讨价,两边拉锯一番,总会成交几笔生意。店家虽非真实的读书人,却对书本的行情十分通晓,遇到买家急需的书本,他会让小伙计火速到某地去取,等候之时,便与客人放言高论,扯起白下书肆的种种闲线年代初,我给北京出书社编那本民国文人散文《江城子——名人笔下的老南京》(后由南京出书社从头出书修订本《金陵旧颜》)时,才在纪果庵的《白门买书记》里,知晓南京书肆从古代至民国的茂盛,其间有一段描绘极为生动有趣:“余最喜听其谈南京书林故事,有开元宫女之思焉。贡院西街在夫子庙,书坊历历,惟问经堂最大,主人扬州陆姓,干练有为,贩书南北,结纳朱门,以乱前萃文书店之伙友,一变而为南京书业之巨头。其人不计小利,而每于大处落墨,又中西新旧杂蓄,故门市最热烈。余买书甚多,不能详记。”读书人谁不喜欢藏书,但像纪果庵这姿态就能够用重金去购书的,又有好多呢?不过,尽管囊中羞涩,能够过眼阅览一下,也是读书人逛书店过过书瘾的嗜好吧,就像女性逛街,看到喜欢的东西,即便不买,也要在手中摩挲一番。

惋惜儿时懵懂,对书没有辨识才能,更不懂得买旧书的趣味和含义。咱们兄弟把压岁钱和零花钱聚起来,去买连环画,虽是下认识的喜爱,却也算是一种保藏吧。我从前是新街口新华书店的买家,成套地购买小人书,最终竟装满了一纸箱,我家也成了玩伴的阅览室。
其实,我在小学三年级时,就开端读小说了,从《高玉宝》开端,随父亲读了许多从大院图书馆里借来的成人书本,历来就不知道要用钱去购书,那是由于读书能够不花一分钱,何乐而不为。
直到1966年时,我才从火中取书中偶得藏书的奥秘与高兴。抢书据为己有,看到了那些不能揭露看到的书本,那种阅览的快感,唤起了我对“藏书”(此为双关)的热心。下乡插队前,咱们撬开图书馆的窗户,入内窃书——那些没有被燃烧的书本,封存也是惋惜了,不如让咱们保藏,带下乡去消遣。这种“窃书”,相似思维“盗火者”的行为,其间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,便是那窃得的《牛虻》,那时,觉得做一个文明“流氓”,并不行耻。后来,当我读到鲁迅《孔乙己》中“窃书不能算偷……读书人的事,能算偷么?”时,心思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,消除了许多罪恶感。
当然,有时我也想着自己攒下生活费去买书。记住第一次去县城新华书店买书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晴朗的秋日,我来回奔走80里的高低圩路,到家现已是一轮新月初上。我不管饥寒疲乏,点上罩子灯,翻开那本郭沫若的新著《李白与杜甫》,一向读到发愤图强时。那本书是我在古诗“创造”期的参阅书本,后来则被我批判过,但至今还孤寂地躺在我的书架上。
大学毕业后,当阅览文学书本变成营生饭碗时,买书就成了粗茶淡饭。那时,我是一条光棍,又有教研室编教材得来的远高于薪酬的外快,所以就将每个月的薪酬划出一半来买书,我真实的藏书年代到来了。不过,跟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很多翻译书本上市,让人耳目一新,我也逐步感觉到囊中羞涩,财力不逮了,尽管那时藏书认识激烈,但毕竟还没到为所欲为买书的程度。
我最为痛快淋漓成捆成捆买书的阅历,是在人民文学出书社修改《茅盾全集》的日子里。韦君宜同意每一个修改能买一部本来供高级干部内部阅览的删节本《金瓶梅》,此外社里还廉价处理了一大批中外著作,各式各样的廉价的书本堆在会计室的门口,咱们像过节得到凭据供给的票券相同,欢天喜地地排队购书。我每相同都来一本,加起来总有几十本,结账后感到浑身舒泰,那是我平生爽快的一桩购书豪举,只不过不是在书店,而是在人民文学出书社的购书天堂里。
从1979年至新世纪初,逛书店成为我假日中的一种休闲方法,尽管每次只购一两本,有时甚至空手而归,却也有精力的满足。那个杨公井的古旧书店,是我常常去的当地,由于夫子庙的旧书摊通过60年代公营新华书店的横扫,几近绝迹,古籍书店也改成了公营的店面,直属新华书店办理。我在此地淘了许多旧书,尤其是专业杂志,像《人民文学》,从1949年创刊号,一向到1977年止的一切各期悉数买下。1957年创刊的《文学评论》(原名《文学研究》)也是从创刊号到1977年的全套装订本都买了。之所以只买到1977年,是由于从那今后我现已自己订阅了这两种刊物。分两次用自行车驮着这些沉重的书刊回家,在书房上架时的高兴,真的是没办法描述。

近二十几年来,我很少再去逛书店了,原因有二。一是许多出书社寄给我的书本和杂志多到无法看完,书刊越积越多,再大的书房,再多的书架,都无法让它们入住了。几回搬迁,只能忍痛割爱,把几千册杂志送人,或许送往收买站。二者,我的逛书店的方法变了,无论是公营新华书店板滞的购书形式,仍是民营书店各式各样的花式出售,都让我心生讨厌,我不肯花费很多的时刻在实体店里,对闲逛书店失去了旧时的愉悦——由于购书的高兴已被网上逛书店所替代,虽没了买家与卖家之间买卖时的言语沟通,没有了现场翻阅和验货购买的典礼感,但是,它带来的却是另一种无尽的高兴。
网上逛书店,不必你去书架上逐个查找或去问询店员,你想购得的书刊,只需轻点一下手机,就会呈现同一种版别的新旧书本几十甚至上百本,不同书店各种价格,让你恣意选择。更让我惊奇的是,书店不单单是卖旧书,即便是全新的书本,也是在网上以几折的价格出售,后来才知道,这也是出书社的出售运营途径之一。当你看到书本以快递方法寄达今后,拆开包装那一刻,心境就像翻开盲盒相同,是走运盒,仍是潘多拉盒呢?
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端,就不再去图书馆借书了,专业书本都是自费购买。当然,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购买所需书本,也是须分主次和等级的。假使是为写文章一次性运用,品相再差的也无所谓,比方前几年为写三部曲批判文章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造原则在我国阐释的演化》,为了阐释张光年的观念,我急需看到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、开展着》初版原文,而非后来收进文集的文字,便在网上搜索到了一本1956年第24期的《文艺报》(胡风事情后,《文艺报》一度改成了装订本),尽管封面现已褴褛不堪,文章的主要内容却是完好无损,原汁原味,甚至能够闻到那个年代的气味,足矣。
又,在写两万多字的长篇漫笔《解救与叛变——重读〈牛虻〉》时,我得找回那个年代的情感,而1968年下乡时带去的那本50年代的初版别,也即“窃”来的那本,早就被其他知青借走,泥牛入海了;故在网上购得50年代那个版别,与后来多个新版别相对照,从中嗅到了不同的年代况味,也是异样阅览的一种无量回味。
在网上逛书店,还有许许多多趣味,成为你回想前史故事的最好桥接。比方,你能够在网上搜索到许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,就像旧年代逛书店的文人,寻找到淘到好书的另一个途径,捡了一个大漏那样欢欣不已。亦如纪果庵所言:“买书不能专走坊肆,街头冷摊、巷曲小店、私家之落魄者、佣保寒贱之以窃掠囤积居奇者,皆不行放过。莫愁路之暗盘,前既言之矣,二三年前,犹可得佳品,近来则绝无。路侧,有曰志源书店者,鲁人陈某所设,其人初不识书,以收破碎零物为业(京语曰“挑高箩”,以其担箩沿街唤买,如北京所云之“打小鼓的”然)。略识之无,同贩中之得书者,辄就请益,见书既多,遂专以收书为事,由担而肆,罗列满架,凡小贩之有书者,咸售于此,故往往佳著精椠。”是的,儿时咱们便是用家里的“废品”,拿到“挑高箩”上换麦芽糖的,在一声拖着长音的“破褴褛棉花——拿来卖”的呼喊后,多少孩子把家里的书拿去换了口福,而没有文明的“挑高箩”者,不会像纪果庵那样识货。
想想现在网上的卖家,多少都是有文明的人,其旧书,除了从出书社刚刚进来的打折货以外,应该有适当一部分是来自废品收买站。收买站里的工人文明程度不高,分拣出来的书本,肯定是会被运营网上书店的老板前来一股脑儿买走的,至于价值几许,那就要凭老板的专业水平来区别等级了。现在网上书店老板的经营规模广了,眼力劲也强了,分类水平也挺高,其签名本的价格成倍翻,尤其是成名的大作家签名本高得出奇。闲时,我常常上网逛书店,阅览这些拍卖的签名本和手札、函件,几张纸的信札标价便是几千块。我从前的一位搭档H君,早年就在网上购得《人民文学》和各个杂志流出来的许多闻名作家的信札和手稿,可谓宝贵材料。他在网上淘到我1985年写给一个学者的公函,赠与我,我回家后,当即将之撕毁,认为无甚价值。
一日,我看到网上有一叠从《文学评论》修改部流出来的签发手稿,那是1986年我和徐兆淮合写的《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递嬗演进》一文,总计29页,是2019年上拍的,居然叫价28800元。谁会当冤大头,去买这劳什子呢?诸如此类开价几千几万元的手稿,至今还有一些挂在网上,无人问津,商家抬价,买家不会容易受骗,此乃市场经济。
常常闲逛网店,偶然也有捡漏的时分。那日失眠,清晨还在网上书店流连,突见我在1988年写的论文《亵渎的神话:〈红蝗〉的含义》(刊《文学评论》1989年第1期)的手稿,一看,是山东一个县城卖家,开价只400元,这却是我乐意收藏的东西,立马拍下,心想,同是鲁人,如纪果庵所说“其人初不识书”,或许连闻名鲁人莫言都不识,轻视了此文的价值,让我得幸敏捷回收材料,由于这篇文章背面,还有一段长长的故事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