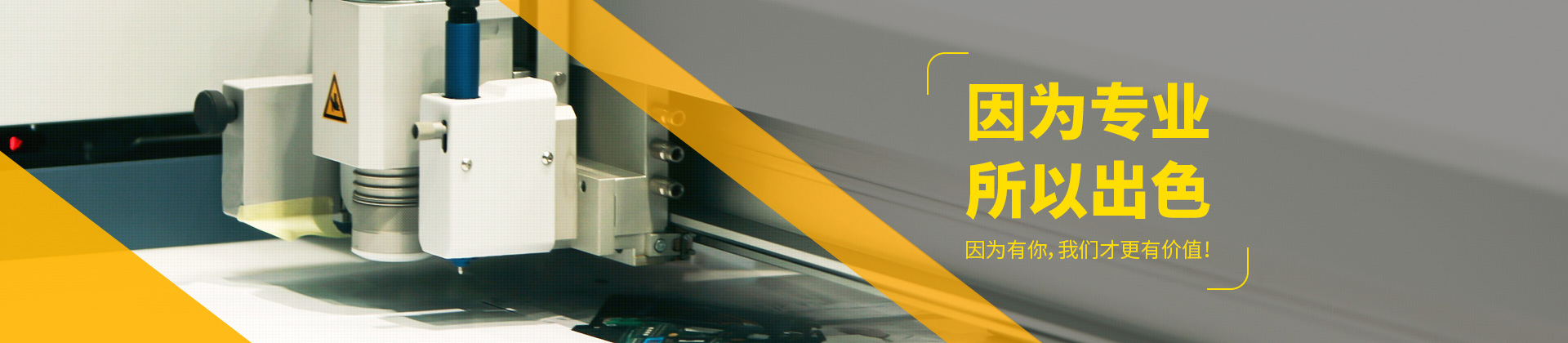老公的誓词犹在耳边,身为女警的林宛君,却在他上锁的抽屉里,发现了一份她毫不知情的遗言。
十八年的丁克约好,十八年的恩爱不疑,在这份怪异的遗言面前,即将被一个没办法幻想的隐秘,完全撕碎。

林宛君的日子,像一杯泡了好久的茶,茶色寂静,滋味醇和,但也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、寡淡的凉意。
由于林宛君办起案子来,那股不要命的劲头,和看穿人心的毒辣眼光,比许多男差人还要凶猛。
“咱们就这么过一辈子二人世界,也挺好。”张建国从前这样握着她的手说,“我不想让孩子来分管你对我的爱,也不想让你本就辛苦的人生,再多一份挂念。”
所以,“不要孩子”就成了他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好,一个牢不可破的盟誓。
他们住在大学分的家族院里,一套一百二十平的三居室,被林宛君拾掇得一干二净。
他们有一同的喜好,喜爱看老电影,喜爱在周末的午后,一人一本书,一壶茶,安安静静地待一下午。
张建国的薪酬不算高,林宛君的收入也仅仅公务员水平,但由于没有哺育孩子的巨大开支,他们的日子显得分外宽余。
可夜深人静的时分,当她完毕一天疲乏的作业,看着身边熟睡的老公,偶然也会有一丝空落落的感觉。
她会下认识地摸摸自己平整的小腹,然后自嘲地笑笑,感觉自己是中年危机,想多了。
她可贵有这样一个悠闲的下午,便想着把老公那间乱糟糟的书房,完全拾掇一下。
她把书本分门别类地从头上架,把散落的稿纸逐个拾掇好,又用湿抹布,将书桌和书架擦洗得锃亮。
就在她整理书桌最底层的一个抽屉时,她的指尖,触碰到了一个硬硬的、方方正正的东西。
当林宛-君看清主页上那两个用三号宋体加粗打印的、黑洞洞的大字时,她的心,没来由地咯噔了一下。
他们是夫妻,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密切的人,产业和身后事,不都应该是两个人一同商议着办的吗?

作为一名刑警,她的工作天性,让她对任何“失常”的工作,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。
她仅仅把那份文件从头放回档案袋,塞回抽屉的最深处,然后将全部康复原样,好像自己从未发现过。
假如这仅仅一份一般的法令文件,他肯定会第一时刻告诉她,甚至会拉着她一同商议里边的条款。
“老婆,我回来了。今天会开得顺畅,几个老教授都夸我前次的论文写得好。”他一边换鞋,一边笑着说。
“是吗?那挺好的。”林宛君从厨房里走出来,接过他手里的烤鸭,尽力让自己的声响听起来和平常相同。
“咦,你把我书房拾掇了?”张建国走进书房看了一眼,有些惊奇,“哎呀,辛苦你了,那么乱,改天我自己弄就行的。”
“没,我看到是锁着的,就没动。”她撒了谎,这是她十八年来,第一次对老公说谎。
“哦,那就好。”张建国松了口气,从口袋里掏出钥匙,走过去“咔哒”一声,把抽屉锁上了。
他这个纤细的动作,和那声细微的落锁声,像一把小锤子,狠狠地敲在了林宛君的心上。
她怕一问出口,那个她尽力保持了十八年的、完美调和的家庭表象,就会像鸡蛋壳相同,瞬间破碎。
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,眉头轻轻皱了一下,然后拿着手机,走到了阳台上,还随手关上了阳台的门。
她听不清他在说什么,只能看到他不停地允许,口气好像有些无法,又有些愧疚。
“哦,我姐。”张建国坐下来,脸色有些不自然,“没什么事,就问问咱们最近怎么样。”

这些年,由于他们夫妻俩不要孩子的事,张兰没少给他们脸色看,话里话外,总是在责备林宛君“占着茅坑不下蛋”,耽误了他们老张家“传宗接代”。
林宛君能明晰地听到身边老公平稳的呼吸声,但她觉得,这个同床共枕了十八年的男人,在这一刻,变得无比生疏。
但现在,在“遗言”这个巨大的暗影下,每一个细节,都被无限扩大,变成了他或许变节了她的佐证。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在地板上投下亮堂的光斑,可她却觉得,整个屋子都冷冰冰的。
一个穿戴警服的小人,在正颜厉色地对她说:“林宛君!你是一名人民差人!你要沉着!你要尊重别人的隐私!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,私自窥视别人的隐秘,是违法的!”
另一个蓬首垢面、满脸泪水的小人,则在歇斯底里地尖叫:“他是你的老公!你们约好了要相守终身!他背着你藏着隐秘,他变节了你!你有必要知道本相!不然你会被逼疯的!”
作为一名差人,她知道,她此时最应该做的,是镇定,是寻觅依据,而不是像一个恶妻相同,用这种方法去求证。
但作为一个女性,一个深爱了老公十八年,却猛地发现自己或许一向活在巨大谎话里的女性,她又火急地想知道,张建国到底在隐秘什么。

那个黄色的牛皮纸档案袋,正静静地躺在最下面,像一个等候被敞开的潘多拉魔盒。
她的目光,跳过了那些繁琐的法令条文和格式化的最初,像一把最精准的手术刀,直直地切向了最中心的部分——产业的承继与分配。
当她的视野,聚集在那几行用打印机打出来的、严寒而明晰的文字上时,时刻,好像在这一刻,被按下了暂停键。
屋子里,只剩下她自己那越来越沉重,越来越短促的,好像下一秒就要中止的呼吸声。